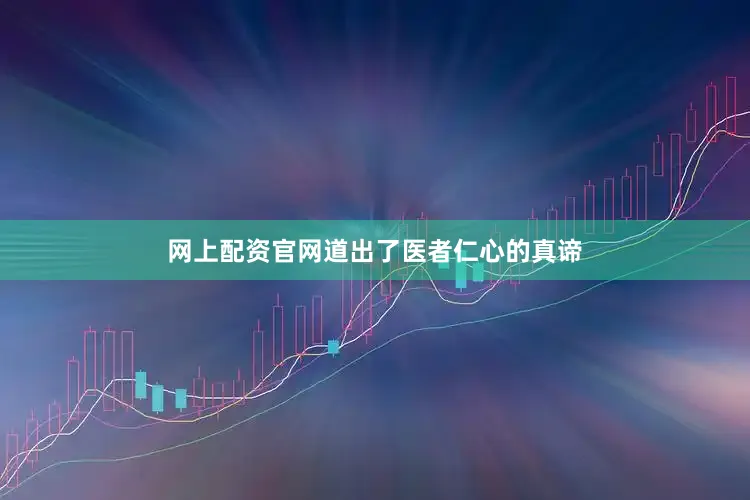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战史探索者 Author 毛豆 123
(注:本文仅从科普角度出发,为保留原意并未对受访者原文进行修改,请读者理性看待,警惕法西斯主义、"极右"思想复活。)

受访者名为莱茵霍特(Reinholt.S),是一名来自武装党卫军第 9 "霍亨施陶芬"装甲师的老兵。他本人于 1941 年志愿入伍,曾在苏联、法国及比利时作战,纳粹德国战败后一度被关押,后于 1946 年被盟军释放。

▲身着迷彩服,手持钢盔准备奔赴前线的"霍亨施陶芬"装甲师士兵,摄于 1944 至 1945 年间
——当被问及 1944 年的诺曼底战役时,莱茵霍特回答称:
啊,那次行动我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们刚在俄罗斯打完春季战役,正在休整。战线相对平静,因为斯大林在重建军队并接收新的补给。我们守着防线,只有零星的小规模战斗;我记得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。期间还帮农民种地,修复被战斗破坏的地方,以此打发时间。
六月份,我们接到向西调动的命令,去增援前线。我们和装甲团一起上了火车,往西走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看到的帝国境内被轰炸的惨状。1944 年,敌人城市的轰炸越来越猛烈,我们有时也因此延误。等我们赶到诺曼底前线时,已经是六月底了,那时盟军已经站稳脚跟。
我知道他们在登陆第一天就向内陆推进了好几公里,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。等我们零零散散赶到时,就被派往卡昂一带的防线,面对英国和加拿大士兵。由于补给问题和机械故障,部队前进的非常缓慢。敌人的炮火支援和空中掩护简直铺天盖地。我们经常被袭扰,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得躲在掩体里。英军发动了几次进攻,但每次都被我们击退,我们几乎没丢一寸阵地。在这儿,我第一次见到了英国战俘,还因此获得了铁十字勋章。

▲一名正给被俘德军伤兵水喝的美军

▲ 1944 年的诺曼底战役期间,因盟军轰炸而严重受损的法国城镇维尔(Vire)
当时我被命令去师部军医那儿检查一块一直没管的弹片。我正穿过一片本应是安全区域的田野,突然听到有人用英语朝我喊。我转身看去,发现是个受伤的英国兵,他在前一天的遭遇战中中弹,因失血过多非常虚弱。我帮他重新包扎了止血带,还给了他水。我英语不好,但他明白我是要带他去治疗。去医院的路上,我们又碰到另一个伤员,我也帮了他,但他走不了路。我已经在扶着那个英国战俘了,就把水壶留给第二个伤员,比划着说我一会儿回来。我们走了两公里才到医院,一到那儿我就报告了俘虏的事,并说还有一个人要救。没有车可用,我只好借了副担架回去抬另一个。医生说这两个人伤得很重,是我救了他们,但有些战友却骂我,说这些英国人遇到党卫军投降时都会开枪。我没理会这些话,只觉得在战争中还能保留点人性挺好的。第二个俘虏给了我美国香烟,那可是稀罕货。
我获得铁十字勋章是因为审讯俘虏时得知敌人正在策划新一轮进攻,这让我们能提前布置防御。我记得那会儿天气很好,晴朗的日子很多,但也招来了更多的空袭和地面进攻。身为装甲掷弹兵,我受过协同坦克作战的训练,但这场新战役主要是防守。只要我们一有动作,立刻就会招来敌军炮火、反坦克武器和空袭。很多坦克还没到达目标就被打瘫了。尽管形势极其不利,我们还是通过有限的反击取得了战果,一度突破了敌军防线。有次反击中,我们缴获了大量补给,还抓了不少俘虏。我身上所有能装的地方都塞满了肉罐头、香烟和咖啡。
我总被敌人充足的物资和装备震惊。我们输就输在这儿——他们有用不完的补给。他们打仗像在玩运动,而不是为了生存。到了八月,我们的防线还是被突破了,被迫撤退。那会儿我受了伤。当时我们的队伍遭到炮击和空袭,我腰部中弹。他们说我很走运,要是晚一天受伤,就会被包围俘虏。我失血过多,时而昏迷时而清醒。后来被送回帝国境内的医院,刚好在伤愈时被派往阿纳姆。

▲一名在头盔上缠绕铁丝网的武装党卫军士兵,推测此举可能是为了方便插上伪装草木
至于阿纳姆战役,莱茵霍特称:
那是盟军夺取莱茵河桥梁的计划,但他们倒霉地空降到了我们休整补充的预备防区。我归队时正好赶上围剿分散的英军并俘虏他们。接着我们冲进镇子,在激烈的巷战中和他们交手。他们把很多房子改造成了堡垒,而且经常不顾里面还有平民。我们既要打仗,又被命令必须特别小心平民。我见过这样一场战斗:我方准备进攻据守民宅和博物馆的敌人。刚调来装甲部队,敌人就扔燃烧弹。我们的高射炮开火,击中了一个正在投弹的士兵,燃烧弹掉进屋里烧了起来。一个尖叫的女人跑出来,后面跟着她父母,我们赶紧撤离了。
那场景太超现实了。攻打博物馆时,队里有个怪人,看到博物馆被用来防守就暴怒。后来他还揍了个英国兵,说那人偷藏了件文物在衣服里。这场战斗里尽是怪事。我们还必须躲避盟军飞机——它们一见移动目标就扫射。我很同情城里的百姓,盟军轰炸铁路枢纽和城镇时,他们只能断电躲在屋里。我们得给民众分发食物,很多人还带着孩子。你看,我们并不像现在人们总说的那样是坏人。我们会尽力帮助敌人,照顾平民。只要有机会,我们就救助英军,他们投降时也给予尊重。虽然不懂英语,但我会给看起来需要的人发烟。这场战斗我只受了点轻伤,算是幸运。

▲正在奥斯特贝克城区内缓步推进的德军士兵

▲(后期上色照)1944 年阿纳姆战役期间被俘英军伞兵
战后我们终于能休整了,被调回帝国重组。那段日子我们帮忙收割庄稼,参观儿童和青年团的营地,同时训练并接收新装备。持续作战的压力让我不堪重负,有次休假回家,家人说我两年老了十岁。
最后,就是 1944 年的"秋雾"(Herbstnebel,即"突出部之役")
莱因霍特:那场战役最终成了我的战争终点。我们向敌军发起了进攻。头几天推进得很顺利,但后来天气放晴,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就来了。我们因此损失惨重。那些被我们称作 " 美国佬 "(Ami,对美军俚称)的家伙补给充足、战斗力强悍。我们没能拿下关键地区,后来被调去增援攻打一个叫巴斯托涅的镇子。那里的火炮、反坦克武器和空袭密集到让任何进攻都成了自杀。我看着漫天飞舞的盟军空投补给,却束手无策。冰天雪地里又冷又潮,打得人绝望透顶。这让我想起俄罗斯战场,不过这里的道路和基础设施要好得多。
我记得当地人对我们越来越冷漠。路上遇到平民时,他们会挥手赶我们走。有次看见辆挂着法国国旗的马车,有个军官上前扯下旗子,大概说这样会招来空军轰炸。那些人嘲笑说德国空军早就不复存在了,还让我们趁早西进投降。虽然怒火中烧,但心里知道他们说得没错。撤退途中,我看到被飞机扫射致死的平民尸体,突然怀疑这些是不是之前那批人——死在他们期待的 " 解放者 " 手里。

▲一名正在检视遇难孩童的美军士兵,摄于 1944 年 12 月的比利时境内

▲巴斯托涅某处医护站门口,担架上停着的美军阵亡士兵遗体

▲一名阵亡在突出部之役中的德军士兵
这次撤退冰冷而压抑。原本被告知这是决定性的西线大反攻,要分裂盟军逼和谈。其实我们只盼着这场该死的战争快点结束,可惜豪赌失败了。撤回德国后再次休整时,我乘坐的火车遭扫射,肩膀中弹。那列军车被打成筛子,旁边停着的民用车厢也遭殃,死了很多平民。后来才知道车上都是要运往山区工厂的东方劳工。
我在医院养伤到四月,驻地已被美军占领。快出院时,他们来搜捕所有武装党卫军。气的是医护人员根本没想掩护我们。起初,美国佬还算人道,后来换防的部队开始肆意虐待俘虏。露天营地里连伤员都得不到医治,我亲眼看着好些人就这样死去。隔壁平民拘留营中,每晚都传来女人哭声,听说只要是纳粹党员家属就会被关进来,很多孩子因此成了孤儿。在那个夏天,还常见喝醉的美军骚扰平民。这段记忆太痛苦,虽然我们投降结束了战争,但战胜者的暴行同样残忍。
有一次,我亲眼目睹一名给生病丈夫送食物的妇女,她刚把面包肉块扔过铁丝网,就被警卫抢走。那女人想理论,却被推倒在地,篮子也被踩烂。她爬起来时,警卫竟朝她脚边开枪取乐。后来听说她丈夫那年秋天饿死了。当时我也染上痢疾,直到 1946 年冬条件才改善。
我们被迫参加 " 去纳粹化 " 学习,看宣传片时稍有不从就会遭殃。虽然 = 终在 1946 年获释,但却永远被打上 " 犯罪组织成员 " 的烙印——这就是我为国效力的下场。

▲被俘德军,摄于 1944 年 6 月诺曼底战役期间
倍享策略-股票平台哪个好用-免息炒股配资-配资中心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